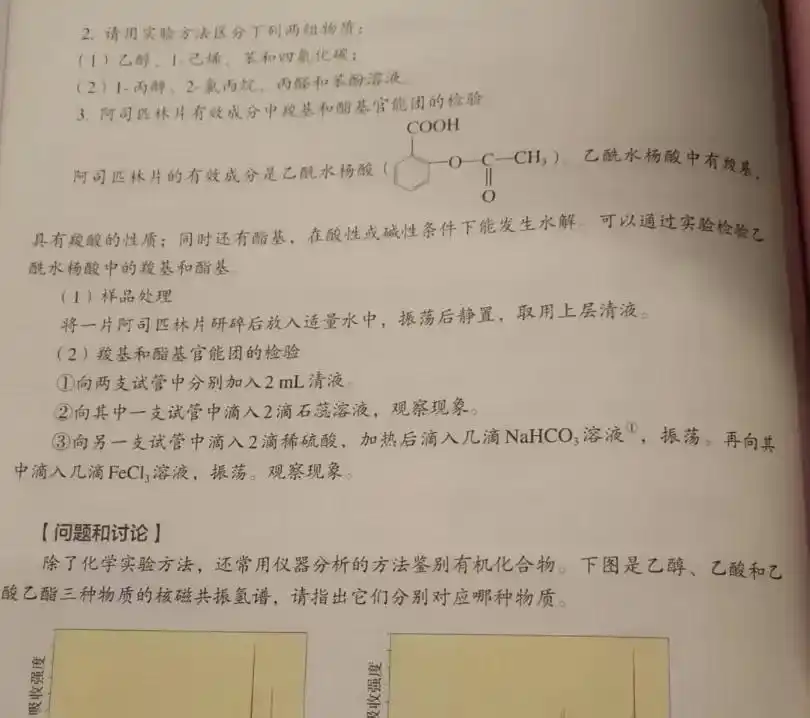| [中医][图文]人民日报专访余艳红: |
 | [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2023年度 |
 | [中医][图文]余艳红已担任国家中医 |
 | [中医][组图]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 |
 | [中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 |
 | [中医]中医院学科专科学术影响力排 |
 | [中医]广东省中医药局公布第五届省 |
 | [中医][图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 |
 | [新知]猪胆主要成分可延缓胆汁淤 |
 | [用药常识]老吃降压药会伤肝肾?打胰 |
 | [骨科验效方][图文]张国恩自拟防活祛湿 |
 | [中医]发展系统中医学,进一步拉 |
 | [趣闻][图文]男童生吃蟹腿寄生虫 |
 | [医药][图文]侯凡凡院士获国际肾 |
 | [趣闻][图文]辟谣:“虎尿”卖每 |
 | [新知]浙八味中药温郁金成分榄香 |
中国加速普及注射死刑,拟全面废止枪决
|
文章导读: |

学者称,全面废止枪决的条件已经成熟
3月11日,成都。一个封闭的室内,“医生”将针头准确无误地扎入“病人”的静脉血管,进入体内的“药水”在两分钟内,结束了三名死刑犯的生命。
这三个人,生前因各种原因杀害了他们的亲友。
如果行刑提前11天,终结他们生命的会是几枚冰冷的子弹。
建国后,枪决一直是中国统一的死刑执行方式。1979年作为执行死刑的惟一法定方式,枪决被正式写入刑法。1996年,新刑诉法补充加入注射作为死刑方式之一。
作为首座试点城市,1996年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死刑。目前,云南、成都、太原全面废止了枪决,另有多个城市计划今年内全面推行。
从枪弹到针头,中国刑罚的人道进步在悄然加速。
刑场归来不敢喝粥与蛋汤
旁观死刑犯的公判大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集体记忆。
死刑研究学者刘仁文对二十多年前目睹的一个场景记忆犹新:一个被捆绑的女囚,脖子上挂着写有名字、打了红叉的木牌,在敞篷卡车上沿当地主干道游街示众一圈后,押往宣判大会会场。下车时,女囚被武警用力一拽胳膊,直接从车上跌滚下来。
1984年,全球已有87个国家废除了死刑。其时,联合国敦促仍延用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
彼时的中国,“严打”正酣,盛行运动式执法。
死囚们在数量庞大的围观者面前接受公判后,直接被拉往刑场执行枪决。对中国北方一些普通百姓而言,枪决死刑犯的作用不仅是政府所宣称的“威慑犯罪,安定社会”:一些人将死刑公告下角的法院公章抠下,缝进体弱多病者的衣服里,以驱邪扶正。
1997年6月初,成都禁毒日集体宣判大会因香港回归而提前。成都某高校刑诉法副教授绉宇(化名)目击了当时的枪决现场。
刑场设在成都东郊,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十余名死刑犯一字排开,各自面向一个小土坡。持枪的武警上前,在半米开外对准犯人脑袋。
枪响,子弹穿透后脑,飞出脸部,溅入土坡。
“有两名死囚倒在土坡上时还在挣扎,武警立即上前补了一枪。”绉宇仍然记得,法医验身后,书记员一一记录“×××,×弹毙命”。
根据刑诉法对死刑执行的程序规定,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对罪犯应当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然后交付执行人员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后,在场书记员应当写成笔录。法院会将执行死刑情况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后,法院通知罪犯家属。
“死刑犯和执行者好像一下子互换了角色。”绉宇说,从那刻起他坚定地反对死刑。
从枪决刑场回来后,绉宇和许多刚上岗的行刑法警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喝粥和蛋汤,这会让他们想起四溢的脑浆。
1996年“严打”高潮过后,宣判大会规模逐渐缩小,次数也开始减少。此外,无罪推定、少杀慎杀等法治理念的普及,剧场式的宣判景观与行刑场面,渐渐退出日常生活。
“贪官的最后特权”?
1996年3月,首座试点城市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作为一种隐秘的执行死刑方式,注射陆续通过解密性的新闻报道,或坊间的传说版本,间接进入公众视野。
曾目睹过注射行刑的一名法官告诉本报记者,被固定在执行床上的犯人,“眼神像临终前的病人一样安静”。注射数秒后,电脑显示屏上的脑电波停止了跳动,变成几条毫无生气的平行线。
注射全程让这名法官肃然而生“专业感”,因为这“不再是对一个有疼痛感的肉体行刑,而是对一个拥有所有权利的司法对象,依法剥夺其生命权”。
据媒体披露,注射行刑共分三步进行。执行法警首先将死囚固定在注射床上,像平常给病人打点滴一样,将针头扎入死刑犯的静脉血管。这项工作一般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医担任;接下来是注射药品,分别为“1号药”和“2号药”,待执行号令一发,执行人员手按“注射键”,两种药水相继注入死刑犯体内。最后,由法医根据心跳、呼吸等来确认罪犯死亡。注射全程不超过两分钟,并伴以轻音乐为背景。
3月1日,成都中院全面推行注射死刑,这让周建中感到兴奋。这名有14年从业经历的前缉毒刑警,对毒贩曾恨不得“拉出去毙了”。改行做刑辩律师后,在死刑短期内无法废除的情况下,他赞成“至少能让他们有尊严地死去”。
让这位律师颇感欣慰的是,他代理的一名女毒贩经其帮助,得以注射方式终结生命。
32岁的女毒贩名叫李华,携枪贩毒43公斤,在狱中不停地哭泣和写诗。周建中清楚地记得,得知通过注射申请时,她说了句,“可以走得诗意一些了”。
西部某高院刑庭的一名法官透露,对于执行注射死刑,院里并无成文标准,而是在实践中倾向于对主观恶意大、社会危害性大的暴力犯罪,采用枪决,毕竟“不能不考虑公众尤其是受害者家属的反应”。
在全面采用注射执行之前,“走得诗意”始终是少数人的幸运。
周建中代理的绝大多数死刑案件,最终仍是被送上枪决刑场。他曾为一名死囚申请注射未果。死囚被枪决后,他陪其父到法院领取骨灰,老人当场哭得失去知觉。
注射的“轻松”,仍然挑战了一些人的思维。据媒体报道,曾有市民致信昆明中院,称“对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来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死法,太便宜他了”。一名癌症患者甚至向昆明中院索要药剂配方,求痛快一死,遭拒后,病人愤然说道:“你们宁对死刑犯仁慈,却不愿成全一个病人!”
注射刑一度还被理解为“贪官最后的特权”,媒体报道中注射刑多适用于中高级官员,如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对此“死亡面前人人不平等”的现象公众一直表示质疑与批评。来源: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