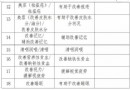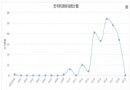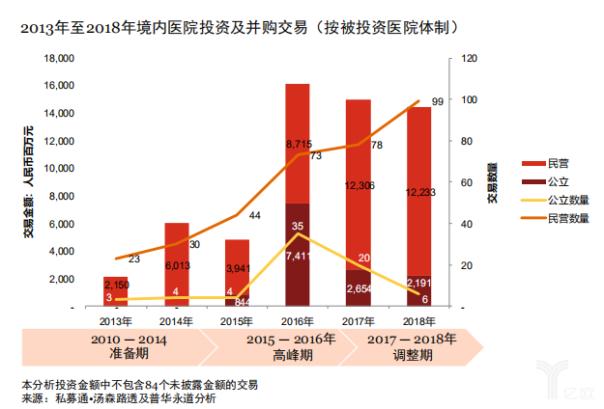广州援交女背后并无悲惨故事 大多引以为傲(图)
|
文章导读: |
据壹周刊报导,广州一个专门提供大学生援交的卖淫集团,租用高级商厦作为办事处,并提供详列200多名大学生图片及资料的花名册。该刊记者追踪,一个“小美”的女孩,经核实就是中*大二年级生。另一个“陈丽”的女孩是广州某外国语学院的学生。
她们认为,问卷答案是胡说八道
斯文是个典型的“乖乖女”,重点中学毕业,她身边最“坏”的孩子都在干些什么,还是“听说”的。“听朋友说过,一些非重点学校的孩子比较叛逆,会迟到、会早恋”,最严重的“还有翻墙”。
她第一次在搜索引擎中敲下“援交”二字时,心里嘣嘣直跳,既害怕弹出的网页会太露骨,也害怕室友们误会。常常开着网页不到三分钟,就要关闭一次,左顾右盼。
她说,这是一个适应过程,到最后,她已经可以大胆地在宿舍里翻阅任何和援交有关的资料了。
寻找援交女孩其实并不费劲,但如何约她们出来则十分困难。没有经验的女孩们被骂了很多回。
开过小会,总结经验后,大家发现,应该先从援交女孩的网络日志入手,从日志中的内容,寻找她们的兴趣爱好,从而打开话题。
但援交女孩的日志总会让斯文看得面红耳赤,“她们很大胆,很多都记录了和客人交易的过程。”说起这话时,她仍有点儿难为情。
连续3个月,这个调研团队四处碰壁,没有成功约到一个援交女孩。
更让大家灰心的是,父母不理解。
斯文不敢告诉父母,只告诉了来广州玩的堂姐,谁知堂姐回家后就告诉了父母。当晚,斯文的妈妈打电话给女儿,一路叮嘱,“和这些女生接触时,一定要少说话”,“不要惹事,或者干脆不要接触更好”。
阿欢的父母反应更大,不给生活费,这样她就没法回广州。
一时之间,调研陷入困境。
其间,幸好她们自己设计的“对援交女孩的态度及认知度调查问卷”在网上渐渐累积人气。
200多个在校大学生、200多个社会人士,共400多人回答了问卷,尽管这距离她们“收集1000份问卷”的目标还有距离,但在当时已是一个不小的鼓励。
但问卷的另一部分进展则十分不顺。问卷结果需要整理给援交女孩看,让她们提出看法,但最终只有4名援交女孩愿意看这样一份问卷。“而且认同感不强,她们认为一些答案很荒唐,甚至是胡说八道。”
骂了24页,于是见面了
转机出现在9月中旬,一份长达24页的骂人聊天记录给这个团队带来了曙光。
被骂的人是调研小组的指导人阿力。
某个快下班的午后,阿力在援交网站上,找到了一名自称是研究生的援交女,这让他眼前一亮。
这名研究生,也成为此次调研中,学历最高的援交女。
“要价多少、在哪个城市、年龄多大了……”阿力习惯先用客人的身份和援交女孩联系,这样能先确定女孩的身份。
这样不会尴尬吗?
阿力一脸坦然地说,“不会啊!我就当做买东西。”他拿起身边的矿泉水,“就当买矿泉水,问问价钱还不行吗?”旁边的师妹偷偷地捂嘴笑。
但当阿力说出真实目的后,女孩连珠炮式的开骂,“×你妈”,“你他妈的”,除了恶毒的谩骂外,逻辑也很强,先质疑阿力的客人身份,再质疑学生身份。
整整30分钟里,阿力不断地道歉,在女孩再次敲来一个“滚”字时,阿力回过去一个“好”字,然后迅速关闭电脑逃离。
他把女生的聊天号码给了阿欢,想着女孩的身份可能更好突破。但第二天,女孩把阿欢也臭骂一顿,然后拉黑。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女孩的头像突然闪了,“在吗?你们那个调研团队究竟想干嘛?”这样一句话,让阿力在电脑前使劲拍掌,“有戏有戏!”果然如阿力所料,女孩愿意出来和他见面。
事后,女孩告诉阿力,她愿意见面的原因很简单,她觉得阿力很老实,怎么骂都不还口。
9月17日晚上7时,阿力和女孩约在一家上档次的日本料理店见面。女孩长发披肩,乖巧斯文,“没办法想象这样一个女孩会是做援交的。”
那一晚,女孩对阿力说了很多。
女孩家住北京郊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做援交既为赚钱完成硕士学业,也用来支持弟妹读书。还有更现实的理由,身边的同学出来工作了、赚钱了,自己希望见面时也能体面点。
为了不让北京的家人发现,女孩打算明年开始在广州租个房子,每个月回来15天左右,专门做援交。
阿力还知道,女孩的脾气很不好,经常被客人投诉。
阿力说,女孩其实很寂寞,很想找个人聊天。他记住了女孩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不欠你的。”
20多岁还用家里的钱,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这个研究团队的幸运还不止于此,同一时间,斯文和阿欢也成功约到了两个援交女孩。其中一个还是中介,正好符合她们的调研要求。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不到1小时,斯文站在女生宿舍的衣柜前纠结,“短袖T恤搭配牛仔裙会不会太幼稚呢?”“还是穿长袖白色衬衫搭配牛仔裤呢?”反复试过几套衣服后,还是没有满意的“成熟装束”。
那时,指针已指向6时30分,斯文决定穿上最休闲的便装,去见那个寻找了三个多月的她。
7时整,斯文在客村地铁站上盖面朝马路的一家快餐店外,先和阿欢碰头,两人相视一笑,表情都有些不自然。
“HI,是你们吗?”斯文尽量让自己语调平淡,希望开场白能自然流畅。
对面的两个女孩实在太普通。做中介的女孩很随意,素颜,简单将染过的卷发扎在脑后,一件格子衬衫、一条牛仔裙。另一个援交女孩则化着粗糙的妆,穿一条黑色连衣裙。
“外表普通,身材娇小,除了说话张扬外,几乎毫无特点,甚至显得有点土。”这是斯文的第一感觉。
接下来整整两个小时的交谈,才真正让她们觉得“不懂”。
“为什么出来做援交?”斯文小心翼翼提出了心中最大的疑惑。
“因为不想花父母的钱,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赚钱,花自己赚的钱。”做援交中介的女孩很认真地看着斯文的眼睛。
她们对于做援交似乎引以为傲。女孩甚至有点不屑地反问:“我真不明白,20多岁还用家里的钱,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斯文和阿欢面面相觑,然后,低头摆弄手里的吸管。
接下来的谈话更加露骨。
她们开始炫耀客人们对她们如何体贴,甚至包括床上的表现。
“她们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能忍到20岁还没有性行为。她们以为我们的世界和她们的一样,十来二十岁有性行为很正常。”阿欢说这话时带着有点颤抖的笑腔。阿欢觉得,尽管是同龄人,但彼此间似乎都不懂对方。
当天晚上,两个女孩彻夜未眠。她们不知道援交女孩究竟在想什么,是什么力量让援交女孩轻易地跨越了她们心里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援交女孩或许也很纠结,她们临走前,也扔下了自己的疑问:“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研,吃饱饭没事干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