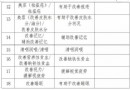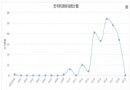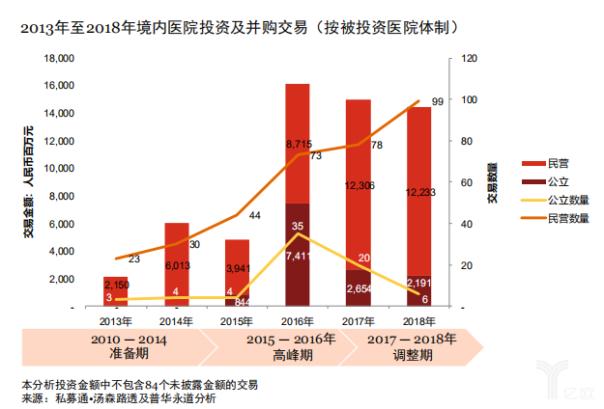自闭症患儿调查:他们被称作冰箱里的孩子
|
文章导读: |
【冰点特稿】:冰箱里的孩子
18双黑亮的眼睛,看上去与别的孩子的眼睛没什么区别。可只有静静地凝望上好一会儿,你才能发现,他们眼睛里倒映的是一个外人无法走入的世界。
这是一群患上了自闭症的孩子。一个8岁正换牙的男孩似乎在看你,他的嘴角甚至浮起了微笑,还做出了拥抱你的姿势,可他扑过来只是死死抓住了你头上的蝴蝶发夹。
一个2岁半的男孩的目光快速地掠过人,然后停留在自己的手上,他把两个大拇指抵来抵去,他比较着相同的指甲,膝盖、鞋子,然后是桌上相同的饭碗、相同颜色的积木。事实上,他比较眼前一切相同的东西。
一个男孩,像追赶着自己的尾巴,不停地旋转,让他停下来的办法是,给他另一个旋转的东西,比如电扇、玩具汽车的轮子,比如画太阳。他可以一刻不停地画太阳,一个又一个,一页又一页……他的瞳仁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圆”。
唯一的女孩,用美丽的大眼睛打量身边的每一个人,突然,这个天使般的3岁女孩,跑到每个人身后,用鼻子闻别人的头发、衣服,然后蹙动鼻翼,做深呼吸——她享受着“闻到的世界”,而不是“看到的世界”。
他们全部身患被称作“精神癌症”的自闭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20分钟就有一个自闭症孩子诞生。
因为眼神冷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被称作“冰箱里的孩子”。在珠海“万香文自闭症康复中心”里,最大的孩子14岁,最小的只有18个月。

25岁的魏卓静静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在他眼里,这些孩子的眼睛,倒映的正是自己的过去。
他是一个曾被宣判“永远不能痊愈”的自闭症患者。大学毕业后,他和妈妈一起,选择成为万香文自闭症康复中心的老师。
“老师,什么是感情?”
身高1.80米的魏卓看起来“健康、正常极了”,珠海市潮热的风吹拂着他柔软的齐肩长发。
灯泡坏了,水管坏了,他上街买零件,运用中学的物理知识修好它们。他上银行存钱取钱,输入密码时,会拿另一只手把键盘罩着。他会看地图,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买电脑内存卡。他知道心疼妈妈,看到妈妈一头汗,会去拿毛巾。他喜欢听周立波的笑话,喜欢看《百家讲坛》。他还是电脑游戏高手,会上网偷菜。
可跟他交谈,只用花20分钟,就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
他不爱接触陌生人,不爱出门,几乎没有朋友。来珠海一年,他没看过海,也没打算去看海。他吃饭总是坐在冰箱前那个固定的位置。他买东西,总是走固定的路线,去固定的店,买同样的牌子,甚至同样的颜色。
他刻板地执行每一项“命令”。妈妈让他买两元钱的菜,他会买上两元钱的西红柿、两元钱的肉、两元钱的黄瓜、两元钱的洋葱——10样菜,不管这个菜是8元一斤,还是5角一斤,他都跟人说:“我只要两块钱的。”
他很少流泪。最心疼他的姥爷死去,他像个没事人儿一样,站在大门口“望了望”。他不知道亲戚这个概念,分不清“表兄”与“堂兄”的区别,也理解不了姨妈的孩子结婚,妈妈为什么要给红包。他说:“这个世界,除了妈妈,谁死了,我也不难过。”
魏卓大学里学的是美术,他最喜欢梵高的向日葵,理由是“形状和颜色很美”。他可没看出梵高的向日葵“像团火”,他面无表情地说:“那是你们正常人的感觉。”
他的导师要他“把全部的感情融入画里”,他说:“老师,什么是感情?。”
他的妈妈、自闭症康复中心的创建者万香文觉得,经过艰苦地训练,儿子已经看起来正常许多,但“他就像一幅高明的赝品,只有对自闭症有足够经验的人,才能发现他还有自闭症的影子”。
自从2009年万香文的自闭症康复中心成立以来,无助的母亲们带着她们同样无助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从澳门过来,比如豆豆的父母,每天要背着他来回两趟穿越人山人海的拱北海关,他们等不及澳门的官办自闭症康复机构,那里有几百人排着队,每个人一周只能轮上一小时。有的从佛山、深圳、香港过来,一个14岁男孩,父亲是佛山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发表过47篇医学论文,但他被孩子的自闭症彻底打败了。还有位家长是大学老师,当他还坐在摇篮旁的时候,他就读着蒙氏教育的书籍,想把孩子培养成科学家,但医生却告诉他,这是个“终身不能痊愈的自闭症孩子”。
根本没有人能说明病因是什么,也没有完善的治疗办法。自闭症,这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就像恶魔一样,每20分钟就伸出魔爪,从地球上抓走一个孩子,不分种族、民族、家长的受教育程度。
从第一例自闭症患者——美国男孩唐纳德于1943年被确诊开始,自闭症已经进入人们生活的半个多世纪。目前,英国的自闭症发生率最高,87个人中就有一个;美国97个人中有一个;日本是112人中有一个。其他国家从1‰~10‰各不相同。各国的统计数据有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诊断的能力。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全球自闭症平均发生率占人口总量的4‰。
我国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调查数据。但按照4‰这个比例数据来推算,我国的自闭症患者约有560万人。
很多家长是第一次从医生那里听到这个名词。他们最初也几乎想象不到,这个医学简称只有“ASD”3个字母的病症,将怎样吞噬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家庭。
万香文是在儿子10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自闭症这个词的,从她在公共厕所看到的一份小广告上,纸上所描述的症状,正是小时候魏卓的症状。后来,她拜访了许多医生,确定了魏卓就是自闭症。
事实上,1985年,魏卓出生时,国内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自闭症这个名词。1978年,北京一个叫王伟的男子成为中国第一例确诊的自闭症患者。1985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医学工作者留学归来,中国大陆才有了自闭症的诊断标准。
几十年又过去了,魏卓、王伟都已成年。如今,王伟跟着妈妈在北京市一个治疗自闭症的康复协会里做义工,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扫地、打水、在发票信封上盖章,还能拎东西到邮局。医生说,他没有走出自闭。相比之下,爱看电影、爱读小说的魏卓要好得多。
他们不是精神病
没人说得清“魔鬼”是怎样抓住魏卓的,即使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脑科大夫也不行。
但可以肯定,当魏卓还是个婴儿,妈妈把《牛津英汉大辞典》给他当枕头,希望他长大成为“大人物”时,这个魔鬼就潜伏在他的大脑里了。
“设想你的世界中,每个声音都像电钻一样刺耳,每丝光线都有如电火花般刺眼,身上的衣物好似砂纸,甚至母亲的面庞看上去也裂成一堆令人恐惧的碎片。”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卡米拉与亨利·马科拉姆这样来描绘自闭症患者的感觉。
从小,魏卓就不愿意被人抱,一抱他就哭,拿手往外推人。他几乎不笑,眼神活泛,却很少与人对视。他喜欢看转动的洗衣机、电扇;喜欢抱着绳子旋转,几乎快勒死了自己;他每天不停地转鸡蛋、苹果、玩具车轮子、比自己还高的大铁锅盖;坐公交车,他哭着要把司机赶走,自己转动方向盘。
小魏卓冷漠极了。他不认识妈妈,不认识家,无数次走丢。妈妈找到他时,抱着他哭,他跟没事人儿一样,冷漠地推开妈妈。妈妈做饭,切了手,烫着了,流着血,他都不会多看妈妈一眼,就像陌生人。
快4岁了,魏卓还不会说一个字。他不知道钱的概念,闻着面包香,就进面包店,抓起来就吃。他行为刻板、重复。无论到哪里,他都会带上一个棍子或者伞,胡乱抡,常把大便打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他只喜欢睡墙角、或者衣柜,哪怕是在家乡吉林省四平市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冬天。他喜欢撕纸,每天不停地撕,直到初中,老师还总是在他的课桌右角处发现一堆纸屑。他每天走相同的路线,换了一条路,就大哭大闹。
这个古怪的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麻烦。他上幼儿园第三天就被退回来。后来,父母离婚,父亲离开家,妈妈万香文不得不辞职回家,24小时照顾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