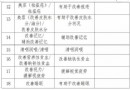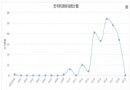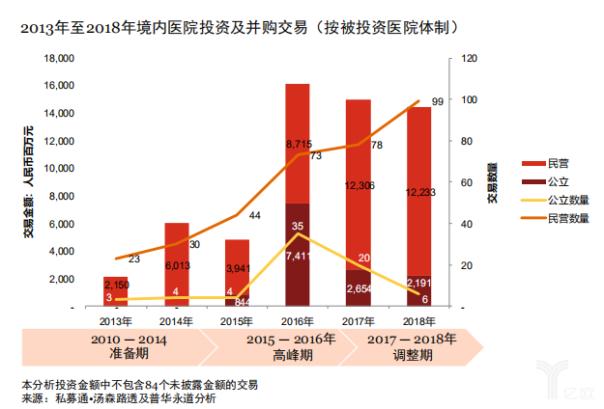广州孝子买农药助偏瘫母亲自杀获刑 亲属为其叫屈
|
文章导读:母亲因为不堪忍受常年的病痛之苦,要儿子去买农药,喝药以后母亲死亡,而照顾母亲多年人称孝子的儿子,却因此成为了杀人嫌犯。 |
邓明建:没问过。
记者:那为什么老妈得病,不用那个(新农合)呢?至少能解决一点困难。
华述英:要住院才报销,不住院不报销。
记者:你婆婆的病严重到那个程度,其实早就应该住院了?
华述英:后来不知道爸爸在家里有没有报销,你不上医院住院,报不了钱。
记者:比如说半边风、中风这样的病,一般来说在农村村里边都会怎么办?
邓明仁:就是像中风、糖尿病、高血压、脑溢血,村里有些得了这些病的人也没有人管,都不在报销范围之内的,都是自己家里在管。
解说:在邓母离开老家前,邓家享受过一年低保每个月能有三十元的低保收入,除此之外邓明建每个月都会给父母和儿子或多或少地寄回几百元的生活费,邓母并不是没有钱参加一年只需要几十元的新农合。我们了解到,在金子乡这样偏僻的山村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一旦得了脑血栓这样的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康复的疾病,只能听天由命。
邓明芳:我婆家那个村里有三个老头,一个老婆婆,四个人中风都只支持了一年就死了,那些儿子就说哎呀不管他,反正看不好,就没有人管他,挨着我们家的第一个院子一个老婆婆,养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中了风没人管她,她孩子说她已经那么大年纪了,他妈也有60多岁了,跟我妈妈同一年中的风,她还是先中的风,只支持了一年就死了,中了风没人管她她瘫在床上,给她吃了点感冒药,看不好就不管她了。
解说:邓母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是在广州度过,邓明建告诉我们他曾经有几次向母亲提起要去大医院看病,他心目中的大医院就是他所租住的石碁镇镇医院。
记者:后来到了番禺以后,有没有带老妈去哪家医院正经八百地去看过?
邓明建:我就想带她去,她不去。
记者:你当时心里准备带她去哪家医院呢?
邓明建:就是去石碁。
记者:像你刚才讲,他现在的收入水平是不大可能把母亲送到大医院去做这种正规的治疗?
刘建明(邓明建的同事):做不了。
记者:像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跟厂里边提出一些求助?
刘建明:没有,这都没有。
记者:如果说他真的提出这种求助的话,厂里边会有办法吗?
刘建明:他也没有说,没有跟工厂提出来,他也知道我们这个企业一个独资的,老板是外资的,说句不好听的,也不是慈善机构,这一点大家都理解。
记者:所以有压力只能自己扛着?
刘建明:是。
解说:患病将近二十年,邓母从来没有去过正规医院做过治疗,而在给邓母看过病的郎中里邓玉昂是惟一一个有行医资格的医生,至今他还保留了十几年前为邓母开的药方,配伍的都是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草药。
邓玉昂:我记得每次开药,好像是几块钱,比较贵的大概是十几二十块钱一次,所以这些年来药费就是要花几万块钱。
记者:我们可以做一个不大可能的假设,假如当初邓明建的母亲到一些条件更好的大医院得到住院治疗的话,可能预后会好一些?
邓玉昂:是,好一些。
记者: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
邓玉昂:哦,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后遗症,这是肯定的,幸好她还能活那么多年,虽然是加重了负担,但是她还是生存下来了。
记者:你妈妈喝了农药以后,给你留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刘建明:她就说了一个谢谢。
记者:你怎么理解这两个字?
刘建明:谢谢,她就说我听了她的话,达到了她的要求。
记者:以前老妈跟你说过谢谢吗?以前你那么照顾她。
刘建明:没跟我说过。
记者:那天这个谢谢是跟你说的惟一的一次谢谢?
刘建明:是,从来没跟我说过谢谢,最后一次说了一个谢谢。
解说:邓明建曾经上班过的鞋厂在番禺区石碁镇的南浦村,工厂在顶峰时有5000多名工人一间工厂带动一个村子是当地的普遍现象,这个鞋厂带动了旁边的南浦村,现在这个村子的外来人口有七八千人,像邓明建这样的打工者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与这个城市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只有在没有订单的时候才会有休息日,自己买菜做饭,基本上不关心自己身边以外的事情,工余时间打桌球是他们最大的娱乐。
记者:这个事情你从头到尾地看起来,纵观这个案子,它有很强烈的这种个人化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里边?
王姗:对。
记者:但是能不能把它归结为一种偶发事件?
王姗:我想可能对于他个人,对于他家庭来说,可能是一个个案的人伦惨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所折射他身上的多维度的身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在当下社会转型期这个特殊的弱势人群,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的压力所迫使他们做出来的选择。
记者: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尽孝多年的儿子,却成为法律上杀害母亲的罪犯,这样一个判决结果清晰地表明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它是不可触碰的,但是是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就可以一判了之?心安理得?显然不是,毕竟邓明建一个人背起重负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得到来自家庭的、社会的足够地分担,而这一点也在清晰地提醒我们,法律制裁是底线,而在底线之前更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有哪些保障和关切是人们应该做,但是并没有做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