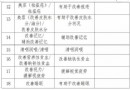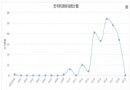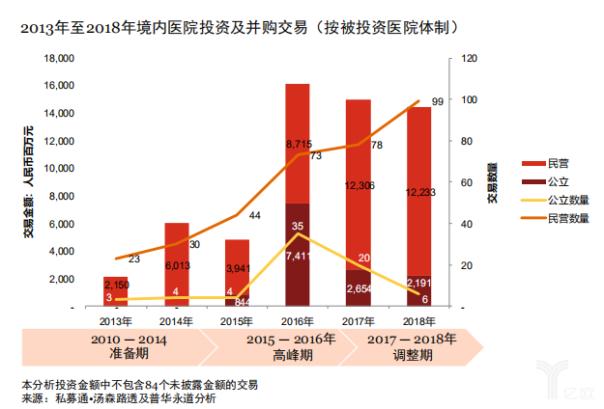抗癌药被污染致残上百人调查:受害者维权遇阻
|
文章导读: |
维权
2007年10月,药害发生3个月。
上海华联药厂委托的律师们,前往各家医院,和受害者们商谈赔偿事宜。
药厂愿支付的赔偿金最高不超过70万,费用中包括已产生的医疗费、后续康复费用、残疾赔偿金等因药害产生的全部损失。部分受害者在等待赔偿时中途病亡,律师给出的赔偿金即时减半。
“这个数额低于不少受害者认为应得的赔偿。”部分受害者委托的律师、曾有多年从医经历的陈北元表示。
谈判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冲突。多位曾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受害者说,药厂委托的律师第一次到医院,给受害者或家属召开会议时,曾公开表示:“赔偿金就这些,你们愿意来谈,就自己来找我,我是不会再来找你们的。”
“这样的赔偿方案,这样傲慢的态度,无法让我们感觉到上海华联药厂——造成这些巨大损伤的责任方,有丝毫内疚之心。”一位至今仍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受害者说,他拒绝和这样的律师协商。
药厂律师提供的《和解协议书》,也让部分受害者不满。协议书上写有“保密义务、禁止反悔”条款,要求受害者在接受赔偿后,不再追求上海华联药厂的任何责任,并且不能向他人透露协议书里的任何内容,若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一位在司法系统工作的受害者家属,当着律师的面撕毁了协议书。
诉讼是受害者们最后的选择。但这同样无法避免因患者中途死亡,赔偿金数额大幅下降的风险。陈北元曾代理齐齐哈尔假药事件受害者索赔案,案件的一审从去2007年3月开始,至今还未有结果,唯一的幸存者任贞朝在一审中途死亡,索赔金额由600万立刻下降至119万。
在谈判开始前,北京的受害者家属老周,联系上了北京40多名受害者,随后又通过朋友在上海找到了50多名病友。“我希望受害者们能联合起来索赔。”老周说。但当药厂律师出现在医院后,每个人的选择多少有些不同。
温尧最好的朋友,29岁的白血病患者小陈,第一时间接受了赔偿。“他病情不稳定,怕父母拿到的赔偿金太少。”温尧说。
温尧的父亲一开始也拒绝这样的赔偿,“儿子也许需要终身护理。”他说。
但温尧愿意。他只想迅速避开这个世界,回到家,躲起来。
他的意愿得到了满足,圣诞节前几天,父子俩在那份写有“保密义务、禁止反悔”条款的《和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孤独者
除了小陈,温尧没有联系任何病友。
离开医院后,他们偶尔会通过手机短信聊聊近况、报个平安。2008年春节前,回老家接受中药治疗的小陈发来了最后一个短信。他在短信中说自己“浑身疼,疼痛从骨头里蔓延出来”,认为这是中药治疗的正常反应。此后,他的手机终日关机。
网络,是温尧和外界进行沟通的最后一个通道。整个白天他都泡在网上,听朋友和同学聊聊工作、女友、聚会。他们大多刚从大学毕业,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太阳落山前,这一切帮助他保持大脑的麻痹状态,温尧说:“只要电脑保持在线,我就可以心情平静。”
在受害者人数仅次于上海的北京,道培医院里,吴志军和温尧的反应恰恰相反,他拒绝接受药厂的赔偿,并称:“腿治不好,决不出院。”
2008年4月,在病友小浦去世后,他成为这家以移植出名的私立医院里,最后一个住院的受害者。
整整一年前,吴志军顺利度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并发症,出院回家。排异反应在他的皮肤上留下紫黑色的痕迹,白血病让他失去了自己多年的生意,但手术成功,意味着他至少保住了命。
他的新生止于甲氨蝶呤。
从2007年夏天再次入院后,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朋友再未露面。“他们可能是觉得我再也好不了了。”这位曾经的吴总说。他现在整日躺在床上,插着导尿管,依靠年过6旬的父亲24小时照料。
他甚至认为,医生已经忘了他的存在。他说:“如果我没有发烧什么的,医生一般是不来我病房的。”
院方多次向他表示,这起药害事故和医院无关,医院也是受害者。而和医生的争论最后总会触怒他。“难道我在商场里摔跤了,还得找地板生产商索赔?”父亲很容易受到迁怒,他冲着父亲大吼大叫,就因为觉得饭菜不适口。“他们都在欺负我,连我爸都欺负我。”他说。
更多的时候,他是平静的,床前的电视机在他清醒的大部分时间都打开着,古装剧、军队文艺联欢晚会,无论放的是什么,他都能看下去。
奇迹没有降临
2008年3月,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叶雯用胳膊撑着床,把屁股转过去一点,坐稳,再腾出手来把腿搬过去,一条接着一条,然后继续撑着床,重复之前的动作。她只是想在病床上换个方向,面对位于六张病床中间的电视机。
在众多成年受害者中,叶雯的康复情况稍好一些。腿出现异样的第三天,这个学习临床医学的女孩,通过网络搜寻,判断问题出在神经方面。父母立刻带着她从江西老家直赴上海,前往神经科最为出名的华山医院求治。
“医生查不出原因,只知道是脊髓神经根出了问题。”叶雯说。医生使用大量激素类药物,刺激她的神经成长。短短两个月内,她的上半身变成一个貌似营养过剩的胖姑娘,下半身,照例是两条纤细到怪异的腿。牵着母亲的手,她能够依靠腰部肌肉的牵扯,走上几步,每一步,都走得缓慢而机械。
年初,母亲带她到北京接受完整的康复治疗。理疗、按摩、锻炼小腿肌肉、大腿肌肉,每周六天,叶雯的康复课程从早排到晚。在这家医院,叶雯每个月的开销是2.5万元。这个数字远超出了她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作为大学生,叶雯通过医疗保险获得的医疗费不过几万元。
大多数受害者,并没有得到像叶雯这样的康复机会。温尧和吴志军,每天只是在家人的帮助下按摩一会腿,然后支撑着架子尝试着保持站立姿式;张庆东的妈妈,每天把孩子抱在儿童自行车上,摇动脚踏板,让儿子萎缩的腿部保持肌肉运动;陈帆的母亲,给孩子买了双高帮运动鞋,把他萎缩变形的脚塞进去,以代替几千元一副的矫正假肢;苗浴光、刘亚明因原有的病情不稳定,必须继续接受化疗,康复需要的大量运动,会影响他们的疾病治疗。
即使有机会接受康复治疗,结果仍是个未知数。叶雯刚进康复研究中心时,主治医生说,虽然没见过像她这样神经受到药物严重损伤的病人,但比起那些因车祸导致神经断裂的病人,她的情况不算最差,也许3至5年可以完全康复。
叶雯对自己也有信心,因为她知道有些受害者身上确实出现了奇迹。2008年初,于静仪的腿部突然长出了肌肉,3月时,4岁的她已能够站立,坐在床上还能摆动两条腿;和周雪住同层病房的张海朋,23岁,在经历了大小便失禁、彻底无法行走后,目前已能扶着墙走上几步。
不过,在经过近3个月的康复训练后,奇迹仍未降临在叶雯身上,而她的主治医生,也收回了乐观的态度。
牵着母亲的手,叶雯能够依靠要不肌肉的牵扯,走上几步,每一步都走得缓慢而机械。
死亡
2008年4月1日晚,小陈去世。
这天到处都有人悼念5年前自杀身亡的港星张国荣,没有人知道温尧最好的朋友死于白血病,去世前,他整日被来自身体内部的剧痛折磨。
早几个月,中日友好医院里,这场药害事件的另一位受害者,年近七十的李治中也去世了。他的女儿和上海华联药厂无法达成赔偿协议,这位老先生至今躺在恒温4摄氏度的7号冰柜,未被安葬。身患淋巴瘤的他,上半身因激素治疗异常肿胀,双腿细如竹竿。
李治中的女儿时时会想到,父亲临死前,挣扎着要站起来的模样。
温尧却说,“我从不思考死亡。”
温尧、吴志军、刘亚明、王美英均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