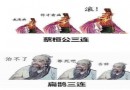| [中医][图文]余艳红已担任国家中医 |
 | [中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 |
 | [中医]中医院学科专科学术影响力排 |
 | [中医][图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 |
 | [中医][图文]王永炎院士:做立大志 |
 | [中医][组图]喜讯!广东新增1名国医 |
 | [中医]2022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
 | [中医][图文]余艳红:充分发挥中医 |
 | [疾病预防]感冒后手脚麻、眼睛花?小 |
 | [纪检]收受药械回扣如何定性?中 |
 | [疾病预防][图文]马上停止佩戴这东西 |
 | [中医][图文]她,是唯一! |
 | [内科杂病]国医大师林天东:治疗慢性 |
 | [医药][组图]南方医院普外科余江 |
 | [纪检][图文]中国工程院院士、积 |
 | [社会]27岁规培生在医院卫生间割 |
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妇人与女体为药
|
文章导读: |
四、结论:「人药」的性别分析
人体部分入药,自古即然而续有发展。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有〈人部〉,其中录人药通计三十五种,自首至足,包括发髲、乱发、头垢、耳塞、膝头垢、爪甲、牙齿、人屎、 小儿胎屎、人尿、溺白(沂土)、秋石、淋石、癖石、 乳汁、妇人月水(附月经衣)、人血、人精、口津唾、齿(沂土)、人汗、眼泪、人气、人魄、 髭须、 阴毛、人骨、天灵盖、 人胞(附胞衣水)、初生脐带、人势、 人胆、人肉、 木乃伊。大致来说,主要为人体自然排出或掉落之物,除人疸之外,并无须开膛破肚者。 然而观诸汉唐之间的医方史传,一则似不以「人药」名之,再则人体部分入药并不限于此。李时珍曰:「神农本草,人物惟发髲一种,所以别人于物也。后世方伎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 其实《本草经》置「发髲」于「虫兽上品」,陶弘景集注时加乱发、头垢、尿溺和乳汁,但分类则未变,仍在虫兽之列。《千金方》所录人体部分入方合药者虽不少,但其〈序例〉中论用药时,却无人药之部,而兽部中也完全未提及人的部分。唐代苏敬《新修本草》〈兽禽部卷第十五〉所收和陶弘景注《本草经》者无异。 学者研究唐代以降民间割股疗亲故事,发现心肝脾肺皆在割取治病之列,而主张亲子之间的血气相感观念是运用此类「人药」的基础。
事实上,传统中国以人体部分入药,大凡小儿生病用父母之物,交接之病则以男用女而女用男。 父母治儿者,如小儿客忤,《千金方》以母亲月衣治之(B27),《外台秘要》则烧母衣带三寸,合发灰以乳汁灌之(B43)。《千金方》治少小腹胀满方,「烧父母指甲灰,乳头上,饮之。」 陶弘景曰:「俗中妪母为小儿做鸡子煎,用其父梳头乱发杂鸡子黄熬,良久得汁,与儿服,去痰热,疗百病。」 此种父、母、子之间的亲子感应在救助难产诸方中尤其明显,不论是横生逆产、胞衣不出、或胎死腹中,丈夫的阴毛、尿液、内衣、裤带、指甲,对产妇、胎儿都有疗效和引导作用。 男女互用者,如前引妇人月布可治所交男子卵缩痉挛;《葛氏方》讨论阴阳易病,主张男子病,「取妇人裈亲阴上者,割取烧末,服方寸匕,日三,小便即利,而阴微肿者,此当愈。得童女裈,益良。若女病,亦可用男裈。」(B18)《僧深方》解释阴阳易病,云:「妇人时病毒未除。丈夫因幸之,妇感动气泄,毒即度着丈夫,名阴易病也。丈夫病毒未除,妇人纳之,其毒度着妇人者,名为阳易病也。」并称「阴易病者,妇人阴毛十四枚烧服之。阳易病者,烧丈夫阴毛十四枚服也。」(B23)放在此一脉络来看,房中养生,男女互用,其理益明。然而,以前文指出养阴之家没落不显,而养阳医方一枝独秀的情况看来,男体部分入药固仍维持,女体为药却以全称式的形态推至顶峰。
合药忌见妇人,过去学者以为主要或因月水不洁。然而以医方涉及性别时用字明确看来,妇人和肢体残缺者、身分过渡者并列,可见其全称式地被视为秽污之属。学者讨论明清战争中的阴门阵,分析传统方书对女阴的神奇信仰,包括以之厌炮克敌。而其机制,难以排除女阴所出的月水、恶露。 江绍原甚具创见的论文虽然题为中国人的天癸观,在讨论时却也无法避免涉及女性身体的其它部分。究其原因,正在于传统医方看待女体的禁忌与功效,其实是全称式而非部分式地思考。前已言及,汉唐之间医方对于月水的主要论述方式并非「污秽不洁」,而是将其视为女弱的源头,并藉此介入女性的生殖与身体。以医方忌见条例并不针对月水而是以「忌见妇人」的行文模式看来,对妇人身体的论述,与其说是对天癸观念的延伸,或不如说是对女体作为一种不完美的存在的禁忌。此种禁忌观念固然主要出现在着名医家的著作中,就现实层面而言,恐非一般医者皆能遵行,然而作为一种文化思维的背景,却可能影响女性合药行医的正当性。
女性史研究近年来文章备出,但亦颇有偏重。最初,主要集中在婚姻制度、守节再嫁,以及知名女性,如女作家和女主等几个主题。之后,平民妇女之婚育生活和职业营生等议题亦吸引学者注意。晚近,则在性别和身体文化的研究风潮下,日渐趋于探讨传统社会对女性之形象表述。笔者近来研究中古女性的医疗照顾及其形象,先发表一文探讨女性行医,近撰一文论述性别与家庭内的健康照顾,而本文则从医方中的女体观念试析女性在医护文化中的形象。综合言之,汉唐之间女性以医护家人表现其伦理角色与性别特质,却未闻有如男性因孝亲习医以致进入主流医疗体系者; 女性以宗教身份和经验累积进行医疗,在民间虽历久不衰,却或受官方节制、或遭医者批评; 女性以观察和身体接触为其医护特色,但其身体则被医方视为污秽之属;女性疏忽家内照护可能遭受谴责,但医疗论述却限制其参与合药;女性既与奴婢、六畜、不具足人并列污秽之属,其身体部分及所沾染之物却被视为具有医疗功效。汉唐之间女性在医疗论述中的主要形象并非能医良工,但以多御童女为主的房中养生观念,却可说将女体为药推至极致。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出入公私、内外领域,在史传医方中则被划地限制、进退两难。描绘此种差异,除了丰富汉唐之间的女性史图像之外,对今日女性研究之学术走向,乃至今日社会对女体的论述,庶几亦具反省之用!
|
|